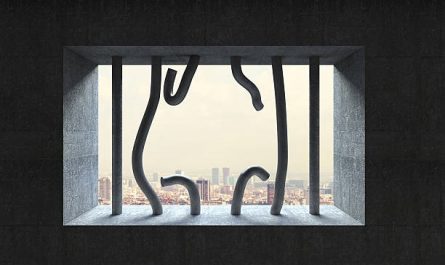在當前情況下,人們的經濟不穩定達到了一個層面和延伸,導致受影響的人不僅陷入貧困,甚至導致社會排斥。到了排斥的階段,還有一步:邊緣化。這種現象不能簡化為社會經濟維度:社會排斥是一種多因素情況,我們從心理和社會干預的角度進行分析。我們將把分析重點放在那些在去社會化之前的一步成為公共服務(特別是圖書館)使用者的人身上。這些用戶構成了一個忠實的群體,但不能免於可能與其他用戶和機構本身發生衝突的特殊性,這既是由於遵守使用規則的困難,也是由於他們要求的規劃和適應需求提供圖書館服務。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深入探討什麼是社會排斥、其類型、例子以及幫助對抗社會排斥的建議。
什麼是貧窮
貧困被認為與經濟不平等情況有關,其特徵是收入水平低於家庭或個人在特定背景下獲得的平均收入的一半或低於一半(Subirats 等人,2004 年)。再往前走一步,就會發現社會排斥。最初,社會排斥與失業狀態和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聯繫的不穩定(在他們內部的邊緣性)有關。
什麼是社會排斥?
社會排斥是多因素的,讓我們想一想,如果不是這樣,即使是在最極端的方面,即貧困,也相對容易解決,因為受影響的人不會錯過任何不會讓他獲得更正常社會功能的機會;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是最有興趣打破這種情況的人。
在許多情況下,社會和公共服務構成了所謂的社會重新融入的最終資源,在去社會化和貧困之前或接近社會化之前。這些公共服務包括圖書館。一定數量的用戶,他們可能知道以前正常化的心理、關係、經濟和社會功能;一旦被剝奪了使它們能夠插入的條件,它們就會崩潰並導致貧困,圖書館是提及正常性或與所述正常性接觸的最後里程碑之一。或者至少,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想法,即使它是虛幻的。
此外,我們將嘗試簡要分析圖書館作為公共空間所發生的過程,該空間歡迎所有類型的用戶,有時,共存存在問題並產生人與人之間的摩擦。
當你進入貧窮時
談論貧困是指與人們及其家庭的經濟標準有關。在西班牙,根據相關人員居住的自治區,存在不一致且多種多樣的非繳費養老金制度。然而,人們一致認為,邊緣化的最終步驟是失去家園。
社會排斥和貧困的類型
就 FEANTSA(歐洲無家可歸者國家組織聯合會)(2018 年)而言,根據 THEOS 類型學,有不同類型的人受到無家可歸和住宅排斥:
到。富夫利斯
- 1. 住在公共場所(沒有家)
- 2. 在庇護所過夜和/或被迫在公共場所度過一天的剩餘時間
b.無家可歸者
- 3. 入住服務中心或庇護所(允許不同住宿模式的無家可歸者宿舍)
- 4. 住在婦女庇護所
- 5. 居住在為移民和尋求庇護者保留的臨時住所
- 6. 住在機構:監獄、醫療機構、無處可去的醫院等)
- 7. 住在支持性住所(無租約)
c. 住房不安全
- 8. 居住在沒有合法所有權的房屋中(非自願地與家人或朋友暫時居住,居住在沒有租約的房屋中——擅自佔地者除外等)
- 9. 放棄財產的法律通知
- 10. 生活在來自家人或伴侶的暴力威脅下
d. 住房不足
- 11. 住在臨時建築或棚屋裡
- 12. 居住在州法律不合適的住房中
- 13. 住在過度擁擠的住房中
如何對抗社會排斥
失去家園意味著“一個人的生活、個人期望和社會結構的深刻破裂”(Márquez 等人,2012 年)。有些群體更注重進行預防,例如:
- 監獄
- 醫療設施(長期護理醫院、精神科治療和戒毒護理中心)
- 兒童保護中心
- 武裝部隊(復員後或從戰鬥或特別危險的任務中返回時)
- 移民(文件與研究中心 -SIIS,2005 年)
儘管存在護理資源,但對無家可歸者進行干預的不同地區之間的社會和健康支持存在很大差異,而且相對低於鄰國(Márquez,同前,同上)。一般來說,它們包括考慮住宿和應對最緊急需求(睡覺、吃飯、淋浴和停留特定時間的地方)的緊急解決方案。在衛生、隱私(浴室、淋浴間、衛生間、公共臥室(與噪音、新用戶的移動和自由空間對接的相關性))、與人身安全相關的問題方面,侵犯用戶需求的行為也經常發生。作為回報,他們被要求有重新融入社會的態度,最低限度的合作。顯然,最可變、最不可量化和最難以接近的過程是那些與街頭人們所經歷的個人結構化相關的過程。因此,在某些情況下,現有的機構做法存在高度失敗,並且不能驅逐它們的地方之一是圖書館在向公眾開放期間的現有空間。
社會排斥和歧視的原因和後果
Jonhstone 等人。(2015) 分析了澳大利亞人口中的歧視與幸福感(在本例中為缺乏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他們確定了影響幸福感和感知歧視之間關係的三個因素,並且有放大後者對前者的負面影響的趨勢。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會解釋為什麼人們感到和看到無助的看法可能是歧視的根本原因,並影響他們所經歷的幸福感。他們表示:
讓污名化成為「可控」的因素
首先,有證據表明,當被污名化的身份被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例如失業、吸毒成癮或肥胖)時,基於群體的歧視對福祉的影響比針對那些具有無法控制的恥辱(例如種族或性別)的人的歧視更不利。事實上,與不可控的恥辱相比,如果針對具有可控恥辱的個人,則個人和肇事者都更有可能認為基於群體的負面治療是合法的(Weiner 等人,1988 年;羅丹等人,1989 年)。
由於住房狀況被視為個人控制之下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無家可歸者經常被追究缺乏足夠住房的責任(Parsell 和 Parsell,2012),並且無家可歸者有可能(更肯定地)面臨高度合法化的歧視形式,放大對他們福祉的負面影響。
對無家可歸者的偏見
其次,儘管無家可歸者被認為是掙扎的,需要照顧和同情(Kidd,2004 年;Benbow 等人,2011 年;Shier 等人,2011 年),但也有證據表明無家可歸者並不被視為完全的人(Harris 和 Fiske,2006 年)。研究表明,無家可歸者作為一個群體不被認為是有能力或溫暖的,因此形成了“最低層中的最低層”(Fiske 等人,2002 年)。這會導致最糟糕的偏見(厭惡和蔑視),並可能使人在功能上等同於物體(Harris 和 Fiske,2006)。 這進一步增加了對無家可歸者進行負面對待的合法性,進而損害了個人應對歧視的能力。
其他污名化的條件
第三,無家可歸者往往不僅因其住房狀況而受到歧視,還因其他原因遭受歧視。特別是,這些人也經常患有精神疾病和/或毒癮,這些情況在社會上受到高度的恥辱(Barry 等人,2014 年)。
總之,由於無家可歸者面臨歧視,這種歧視被認為是出於許多不同原因攻擊他們的合法性,因此我們預測無家可歸者的福祉將受到負面影響。與此一致的是,定性和定量工作都描述了無家可歸者歧視對其福祉的負面影響(Phelan 等人,1997 年;Lynch 和 Stagoll,2002 年;Kidd,2007 年),無家可歸者將歧視經歷描述為使從無家可歸者到就業和穩定住房的過渡變得更加複雜和具有挑戰性(Milburn 等人,2006 年;Piat 等人,2014 年)。如果沒有,就不可能。
歧視中的污名化
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體驗到它,以及我們如何無意識地、不必要地利用這些歧視機制,即“正常化”群體,我們這些有幸克服逆境的人。德克勒克教授在他的《漂流者》一書中揭露了這一點,他指出了在治療師和患者之間實現認同的困難,而後者(已經被擊敗並放棄了所有希望)開始了他的墮落和沉淪(專業人士如何逃脫,尋求失去自己的身份,消失):
「凝視的這一維度指的是社會與街頭人口相關的話語的一個經典主題:它是乾淨和骯髒的主題。社會身體的無住所、殘留物是它的恥辱,玷污了它的空間。面對這種混合瘟疫,這種混合瘟疫傳達了一種對安全和審美不便的痛苦,重要的是「清潔」空間,將無住所的人轉移到社會上(如果不是地理上)遙遠的其他地方。他們的光是視覺是不合時宜的。有必要將它們從凝視中偷走,這是一個健康的空間,簡而言之,它不能再在無瑕疵的視角中找到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東西,即空虛的,也就是說,死亡……」第 240 頁。
對括約肌缺乏控制,德克勒克教授(同前引文)在精神分析解釋中給出了價值:他將這種行為歸因於與他的身體和時空身份的破裂的關係。通過隨意行動,主體中內在性和身體外在性之間的穩定身體闡述消失了:通過這種方式,個人發現自己被放逐出世界及其需求、時間、空間、他人和他自己。詩意,但悲劇。同時,它是一種工具,他用來首先忽視周圍的人,然後驅逐他周圍的人,同時在他的環境中佔有空間(“噁心”、“可怕的氣味”)。他破壞了社會秩序,他是卓越的違法者,與罪犯、吸毒者、一起(有時角色重疊和共享)。 在這裡,我們進入了感到委屈的“正常人”(被氣味視為對我們乾淨天堂的侵略),但被指控的侵略者不明白為什麼(已經適應並且沒有自我感知他的身體和物品散發出的氣味)。
但為了「幫助」他們擺脫這種狀態,這些無住所的人必須提出請求,並提出他們無法隨著時間的推移維持的要求(他們已經廢除了他們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方式)。首先,他們需要提供某種類型的文件,這些文件是他們經常丟失的(例如自我懲罰,因此他們更關心他們的嬰兒車、睡卡而不是文件),並重新申請以獲得任何類型的援助的資格,但由於他們缺乏此類文件而無法提供給他們。對於生病、去社會化的人來說,這是一項巨大的努力,他們不明白對他們的要求,但一旦被要求,他們也已經失去了它。一個無休止的地獄循環,對受影響的人造成痛苦,而善意的幫助者則受到某種蔑視。
圖書館作為幫助對抗社會排斥的資源
圖書館是卓越的應急空間之一:配備照明、暖氣、可公共通道的廁所,可以在進入和離開之前與附近的一些用戶和公眾互動。但除此之外,它們現在是而且可能是沉浸在貧困中之前將人轉變為“景觀和城市家具”的最後機會之一。當然,這些人是極少數和異質的部分,他們要求圖書館可以為他們提供部分公共服務(Fitzpatrick Ass,2004)(他們甚至不要求這些服務,他們就在那裡)。這些用戶是未完全同化的人,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能力、社會地位或離開了以前的文化,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被拒絕或無法在他們所生活的新社會中被完全接受。從這個角度來看,失去社會地位的主體通常會成為相對於多數群體的未分化少數群體的一部分,據稱是正常化的(Meneses,2008)。
因此,基於實習的個人經驗,在時間價值和觀察到的設施數量有限的情況下——文獻學院的實習——使我們能夠在兩個維度上做出一些欣賞,這可能需要更大的方法論深化。
用戶
第一個是指用戶,區別非常簡單,可以輕鬆區分:
- 在經濟和社會上暫時處於不利地位的用戶(包括路人、失業但試圖重新融入社會)。
- 我們可以認為在圖書館內的行為和使用圖書館設施方面更勤奮(具有更永久性質)的用戶。
首先,他們的不穩定程度是根據他們的經濟狀況而區分開來的——在第一種情況下,與完全缺乏資源和對準時到達施粥處和住宿的擔憂相比,他們沒有工作,福利耗盡。
健康因素
其次,我們看到它們的健康因素存在差異:
- 在第一種情況下,通常保留或輕微受影響。
- 在存在身體和/或心理健康問題的情況下,在第二種情況下;除了不同的行為之外:勤奮者尊重規則,而使用和行為規則則更加寬鬆,對於最被剝奪的人。
文化和教育因素
第三,在文化和教育因素方面存在差異:雖然弱勢用戶努力根據可用資源獲得、發展和維持新的技能和能力——使用機構和立法公告、可用社會服務資源、信息通信技術、彌合數字鴻溝的嘗試(作為一種工具,也是一種工具, 作為一種愛好,甚至有一個虛擬的固定地址、郵箱)。
另一方面,第二種是被剝奪繼承權,如果他訴諸服務來庇護自己,利用對 ICT 的愛好——感興趣,或者更常見的是,完全不感興趣(佔據一個有一定程度舒適的地方,在計算機或視聽領域)。
生活環境
第四個觀察結果是指區分它們的重要情況:勤奮使用者的就業狀況、家庭核心(最近離婚或分居、子女監護權衝突、因經濟因素移民而離家的距離);面對冷漠、與環境和可用資源的脫節。
機構態度
評估的第二個維度是與機構本身和其他正常使用者對這些人所表現出的態度有關,以及從這些人那裡接受和機構提供的待遇,這無疑對他們的精神和身體狀態產生影響。
註解
根據直覺,如果沒有觀察性的,而不是定量的,我們可以說“軼事”方法,但所有這種性質的中心都在重複這種方法,我們已經看到,這個設法通過公共圖書館門檻的受歧視的、少數的、異質的群體提出了問題,一般來自:
- 經濟因素(缺乏工作、缺乏資源)
- 健康因素(身體和行為和/或兩者兼而有之)
- 教育和文化因素(缺乏新技能和能力、信息通信技術等,如果不公開,絕對不感興趣)
在他們身上,所謂的數字鴻溝清晰可見:他們嚴重無法從他們所掌握的資源中賺取一點利潤(當他們被允許時,他們將它們用作一種愛好——音樂、電影;而不是作為允許他們擁有固定虛擬地址的工具——要么作為他們可以接收信息的郵箱,而不是最終與可用資源或可以使他們受益的信息斷開連接。
此外,他們之所以達到這種狀態,是由於生活、個人、生命的多種環境因素(長期失業、離婚、失去監護權、出獄、濫用藥物的消耗、公共援助管理不力等)。
與機構和其他用戶相比,這種狀態使他們處於劣勢。他們因缺乏身體衛生和個人外表而遭受歧視,因行政狀況(沒有固定地址或沒有旅館地址)而遭受歧視。政府以極大的善意向他們提供幫助,但面對對服務正常運作的干擾(關於如何行動的協議,以什麼方式——有時他們以不屑一顧的方式或口頭攻擊性——採取什麼行動)。他們是具有差異特徵的用戶,這導致他們對行政部門和自己的員工不感興趣。他們甚至經常被降級為展示小禮物(機構營銷、競賽、會議、鋼筆、隨身碟等)的旁觀者,這些禮物提供給其他用戶,他們對此表現出完全不感興趣,他們不再抱怨)。
協助對抗社會排斥的介入措施
儘管當前時刻非常複雜,但不幸的是,許多用戶將消失(習慣的喪失、歧視的加劇、背井離鄉的更大程度),但該部門的行政部門和工作人員似乎有必要在市政技術人員和社會服務機構的支持下,努力提供這些用戶可能需要的公共服務。
人們可能想知道一個人是否可能沒有經歷過與以下內容相關的事情:
- 非常基本的免費資訊和數位素養(不涉及額外費用)
- 辦公工具處理TXT、Word 和互聯網:管理郵件和充當數字地址的網站(附加、下載、保存等)。
- 制定規則:很少,非常明確,在應用時不太自由裁量。
- 不要歧視或依賴值班工人。
- 為員工提供持續的培訓,了解在特定和特定情況下必須向公眾提供的治療。
- 起草用戶權利法案或用戶服務良好實踐準則(以及旨在預防和保護工人的行動(潛在有害物體、接近和稱呼用戶的態度或方式、距離、肢體語言等)。
本文僅供參考,我們無權做出診斷或推薦治療方法。我們邀請您去找心理學家來治療您的特定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