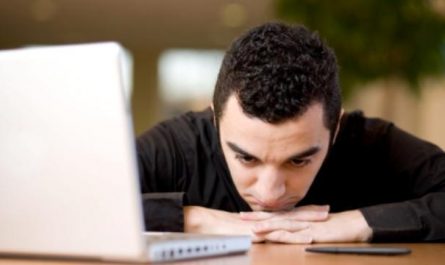一個非常常見且危險的偏見,因為它為大多數人所知,是所謂的“事後偏見”,它由事後判斷的錯誤組成。也稱為事後諸葛亮或概括偏差。它是強調最近記憶的一種效果,通過說服你你已經預見到一個事件,但這個事件已經知道甚至已經發生過而被啟動。當你說 “我這麼說 ”之後,而不是之前。”這個過程遠離現實,接近誤解和關係問題;事實上,你沒有預見到它,你認為你預見到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深入探討什麼是後見之明偏見、它的特徵以及這方面的一些例子。
什麼是事後偏見?
事後偏見是什麼意思?事後偏見的概念來自心理學文獻,特別是來自實驗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後驗的人誇大了他們在事件發生之前所知道的:這就是“我一直都知道”效應。事後偏見是重建過去的傾向,使其與當前知識的包袱相容:簡而言之,這是一種可以追溯到過去的確認偏見。一旦事件發生,我們就會重建它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它會以這種方式發生而不是另一種方式,以及為什麼我們應該預見到它。我們都是好教練,但在比賽之後。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的大腦通過想法的模式和聯想進行推理,這樣,每當我們可以將結果與原因聯繫起來時,大腦就會將它們合併成一個有用的可重複模式,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面對類似情況時再次使用它並幫助我們預見它。
為了更好地理解偏見,在本文中,您將通過示例找到什麼是認知偏見。
事後偏見的特徵
事後偏見在一場重大災難后全面表現出來,當每個人都認為他們知道它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為什麼會發生,以及為什麼專家和領導者應該預見到它。不可能和不可預測的事件不僅變得可能,而且在之後幾乎是肯定的。災難過後,回想起來,一切似乎都很簡單,分析案件的“專家”想知道所涉及的主題是如何沒有注意到明顯的聯繫的。
事後偏見還有另一個方面,稱為結果偏差:當結果不利時,那些重新審視案例的人更有可能批評所給予的關注並發現錯誤。例如,Caplan 及其同事 (1991) 要求兩組醫生回顧一系列臨床記錄。兩組的評分相同,但患者結局相同,一組評價員滿意,另一組評價員較差。不良結局組的批評比另一組嚴厲得多,儘管所描述的治療方法相同。因此,事後看來,我們簡化了事情,並且在退出不利時往往會更加批判。
事後偏見的例子
讓我們看看這些認知偏差的一些示例:
- 陰謀。事後偏見在陰謀論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陰謀論通常基於一個結果,根據現有證據,這個結果不容易預見,但無論誰負責干預,都不會這樣做。這意味著一切都是預先程式設計的。想想 9 月 11 日的襲擊,根據陰謀者的說法,根據所有可用的證據,美國人似乎不可能不知道這次襲擊,因為他們手裡掌握了推斷它的所有要素。
-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後偏見的例子是珍珠港事件:根據陰謀論來源,事實上,在襲擊發生前的幾天裡,已經有多達八份報告,這些報告是日本指揮官通過無線電攔截的結果,關於夏威夷基地即將遭到襲擊。由此,陰謀者推斷,這次襲擊是很容易預見的,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有預謀,旨在成為干預戰爭的藉口。實際上,這種敘述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同一天里,日本指揮官的無線電竊聽截獲了 58 條與日本船隻在菲律賓的動向有關的資訊,21 條關於巴拿馬的襲擊,7 條關於印度和東南亞的襲擊,甚至 7 條可能襲擊美國西海岸。因此,當時的攔截是如此之多,令人困惑,以至於「軍事情報部門不再向白宮發送備忘錄,擔心安全系統會遭到破壞,日本人會開始懷疑美國人破解了他們的密碼,他們正在閱讀他們的通信。
本文僅供參考,我們無權做出診斷或推薦治療方法。我們邀請您去看心理學家來治療您的特定情況。